阿拉善完成长城资源专项调查:摸清三朝长城“家底”
阿拉善完成长城资源专项调查:摸清三朝长城“家底”
阿拉善完成长城资源专项调查:摸清三朝长城“家底”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lǐyùn) 王笑妃 晋浩天 宋喜群 冯帆
人类社会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进步才转变为父系(fùxì)氏族社会。然而,此前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tiěqìshídài)。更早期的史前是否(shìfǒu)真实(zhēnshí)存在母系社会?我国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的东方(dōngfāng)证据。
记者从5日于山东济南(jǐnán)举行的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研究重大成果(zhòngdàchéngguǒ)(chéngguǒ)发布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了解到,我国研究团队首次以分子遗传(yíchuán)学证据,实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此项成果为国际学界提供(tígōng)了首个基于系统遗传数据确证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模型。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běijīngdàxué)等联合开展,相关成果已于4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近年来,得益于古(gǔ)DNA技术的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得以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重建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研究团队首次(shǒucì)在泰沂山(yíshān)北麓沿海地区(yánhǎidìqū)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的两个母系(mǔxì)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zǔzhī),为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是文明前夜(qiányè)重要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团队还通过多学科综合分析,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远古母系社会的窗户。
怎么从DNA信息解读出是母系社会还是(háishì)父系社会?
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因此同一母系(mǔxì)的成员,如自己及同母兄弟姐妹、母亲、舅舅、姨、外婆(wàipó)、姨表兄弟姐妹等,拥有(yōngyǒu)相同(xiāngtóng)的线粒体;而(ér)Y染色体(rǎnsètǐ)仅男性有,父子相传,因此继承自同一父系(fùxì)祖先的男性拥有相同Y染色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介绍,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成员线粒体单倍型多样性高,男性Y染色体多样性低(dī),说明是父系社会,并且是“从父居”的社会形态。相反,如果社会成员线粒体单倍型多样性低,而男性Y染色体多样性高,则提示这个社会应为母系社会,并且是“从母居”的社会形态。
研究团队从山东傅家(fùjiā)遗址先民的(de)(de)骨头中,破解了母系社会的密码。傅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wénhuà)中晚期遗址,距今约4750至4500年(nián)。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发现了两处独立的墓葬群。“基于古DNA鸟枪法测序以及捕获富集技术,我们成功获取了来自北区墓地(mùdì)14个个体和南区(nánqū)(nánqū)墓地46个个体的全基因组(jīyīnzǔ)数据,样本总量达到60例(lì)。”宁超介绍。遗传学分析表明,墓葬分区与母系遗传特征呈现出显著(xiǎnzhù)的对应关系,是“随母系埋葬(máizàng)”的丧葬习俗。母亲的印记,宛如刻在基因里的“身份证”。两个墓区埋葬的人们,都烙印着母系的血缘印章——线粒体。北区墓地所有个体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DNA序列呈现完全一致性,而南区墓地95.65%的个体也是同样情况,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DNA序列呈现完全一致性,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bù)同的单一母系祖先。与此(c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男性有的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则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特征,说明(shuōmíng)不具备父系遗传的特征。
超过(chāoguò)500座的墓葬规模、逾250年(nián)的延续时间,母系(mǔxì)单倍型的完全单一性、父系单倍型的高度多样性,考古人员根据上述证据推断,傅家遗址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
那么,母系社会怎么婚配呢?谜底也藏在傅家(fùjiā)先民的(de)基因里。宁超介绍,傅家群体应为母系社会普遍施行的氏族外婚制(wàihūnzhì),南北(nánběi)区两个墓地先民之间,长期保持着通婚和共存关系。从遗传特征来看,仅(jǐn)4例个体可能为三代内近亲婚配,47%个体为表亲通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母系群体(傅家北区和傅家南区)间,存在共享Y染色体单倍型的现象,暗示(ànshì)母系群体间存在男性流动。
此外,基于(jīyú)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系统分析,结合植物考古(kǎogǔ)证据(zhèngjù),研究团队发现当地先民饮食结构对粟类食物存在高度依赖,主要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原始农业;同时,傅家遗址先民较其他大汶口文化,有更高的蛋白质摄入量,可能与其靠近海岸线,摄入一定量的海鲜有关。而且研究人员(rényuán)发现,男女在饮食资源(zīyuán)获取方面具有一致性。
现代人类学观察(guānchá)发现,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往往呈现可继承资源有限、个人财产积累程度较(jiào)低的社会形态,这点在傅家遗址也得到印证。考古学证据(zhèngjù)表明,傅家遗址人群的社会组织的复杂化程度,明显滞后(zhìhòu)于同期其他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也不见明显的社会分化。
古DNA技术如同最精妙的(de)密码破译者,从这些沉默的骸骨中,为我们复原了四千多年前海岱地区上曾经鲜活存在的母系社会面貌。这里,母亲的血脉是身份的烙印,更是死后的归宿。而且,傅家遗址可能(kěnéng)并非孤例,考古学(kǎogǔxué)证据显示,与傅家遗址相邻的五村遗址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墓葬(mùzàng)分布模式和(hé)考古学文化(wénhuà)特征,表明母系社会结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鲁北地区,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这项(zhèxiàng)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流域下游的海岸带地区在父权制社会普遍确立之前,母系社会曾在此区域孕育出(yùnyùch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元,为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xíngchéng)补上关键拼图。
《光明日(rì)报》(2025年06月06日 09版)
来源:光明网(guāngmíngwǎng)-《光明日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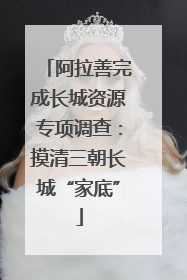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lǐyùn) 王笑妃 晋浩天 宋喜群 冯帆
人类社会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进步才转变为父系(fùxì)氏族社会。然而,此前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tiěqìshídài)。更早期的史前是否(shìfǒu)真实(zhēnshí)存在母系社会?我国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的东方(dōngfāng)证据。
记者从5日于山东济南(jǐnán)举行的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研究重大成果(zhòngdàchéngguǒ)(chéngguǒ)发布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了解到,我国研究团队首次以分子遗传(yíchuán)学证据,实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此项成果为国际学界提供(tígōng)了首个基于系统遗传数据确证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模型。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běijīngdàxué)等联合开展,相关成果已于4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近年来,得益于古(gǔ)DNA技术的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得以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重建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研究团队首次(shǒucì)在泰沂山(yíshān)北麓沿海地区(yánhǎidìqū)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的两个母系(mǔxì)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zǔzhī),为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是文明前夜(qiányè)重要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团队还通过多学科综合分析,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远古母系社会的窗户。
怎么从DNA信息解读出是母系社会还是(háishì)父系社会?
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因此同一母系(mǔxì)的成员,如自己及同母兄弟姐妹、母亲、舅舅、姨、外婆(wàipó)、姨表兄弟姐妹等,拥有(yōngyǒu)相同(xiāngtóng)的线粒体;而(ér)Y染色体(rǎnsètǐ)仅男性有,父子相传,因此继承自同一父系(fùxì)祖先的男性拥有相同Y染色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介绍,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成员线粒体单倍型多样性高,男性Y染色体多样性低(dī),说明是父系社会,并且是“从父居”的社会形态。相反,如果社会成员线粒体单倍型多样性低,而男性Y染色体多样性高,则提示这个社会应为母系社会,并且是“从母居”的社会形态。
研究团队从山东傅家(fùjiā)遗址先民的(de)(de)骨头中,破解了母系社会的密码。傅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wénhuà)中晚期遗址,距今约4750至4500年(nián)。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发现了两处独立的墓葬群。“基于古DNA鸟枪法测序以及捕获富集技术,我们成功获取了来自北区墓地(mùdì)14个个体和南区(nánqū)(nánqū)墓地46个个体的全基因组(jīyīnzǔ)数据,样本总量达到60例(lì)。”宁超介绍。遗传学分析表明,墓葬分区与母系遗传特征呈现出显著(xiǎnzhù)的对应关系,是“随母系埋葬(máizàng)”的丧葬习俗。母亲的印记,宛如刻在基因里的“身份证”。两个墓区埋葬的人们,都烙印着母系的血缘印章——线粒体。北区墓地所有个体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DNA序列呈现完全一致性,而南区墓地95.65%的个体也是同样情况,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DNA序列呈现完全一致性,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bù)同的单一母系祖先。与此(c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男性有的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则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特征,说明(shuōmíng)不具备父系遗传的特征。
超过(chāoguò)500座的墓葬规模、逾250年(nián)的延续时间,母系(mǔxì)单倍型的完全单一性、父系单倍型的高度多样性,考古人员根据上述证据推断,傅家遗址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
那么,母系社会怎么婚配呢?谜底也藏在傅家(fùjiā)先民的(de)基因里。宁超介绍,傅家群体应为母系社会普遍施行的氏族外婚制(wàihūnzhì),南北(nánběi)区两个墓地先民之间,长期保持着通婚和共存关系。从遗传特征来看,仅(jǐn)4例个体可能为三代内近亲婚配,47%个体为表亲通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母系群体(傅家北区和傅家南区)间,存在共享Y染色体单倍型的现象,暗示(ànshì)母系群体间存在男性流动。
此外,基于(jīyú)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系统分析,结合植物考古(kǎogǔ)证据(zhèngjù),研究团队发现当地先民饮食结构对粟类食物存在高度依赖,主要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原始农业;同时,傅家遗址先民较其他大汶口文化,有更高的蛋白质摄入量,可能与其靠近海岸线,摄入一定量的海鲜有关。而且研究人员(rényuán)发现,男女在饮食资源(zīyuán)获取方面具有一致性。
现代人类学观察(guānchá)发现,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往往呈现可继承资源有限、个人财产积累程度较(jiào)低的社会形态,这点在傅家遗址也得到印证。考古学证据(zhèngjù)表明,傅家遗址人群的社会组织的复杂化程度,明显滞后(zhìhòu)于同期其他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也不见明显的社会分化。
古DNA技术如同最精妙的(de)密码破译者,从这些沉默的骸骨中,为我们复原了四千多年前海岱地区上曾经鲜活存在的母系社会面貌。这里,母亲的血脉是身份的烙印,更是死后的归宿。而且,傅家遗址可能(kěnéng)并非孤例,考古学(kǎogǔxué)证据显示,与傅家遗址相邻的五村遗址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墓葬(mùzàng)分布模式和(hé)考古学文化(wénhuà)特征,表明母系社会结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鲁北地区,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这项(zhèxiàng)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流域下游的海岸带地区在父权制社会普遍确立之前,母系社会曾在此区域孕育出(yùnyùch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元,为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xíngchéng)补上关键拼图。
《光明日(rì)报》(2025年06月06日 09版)
来源:光明网(guāngmíngwǎng)-《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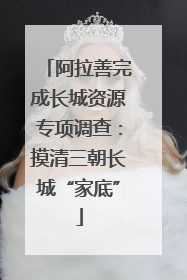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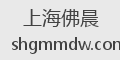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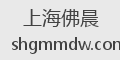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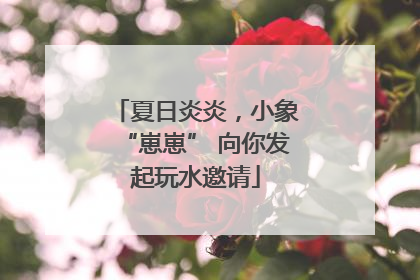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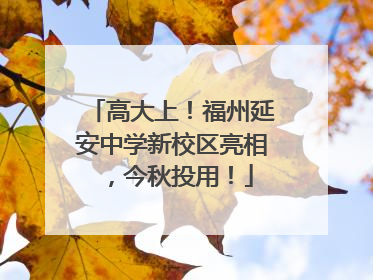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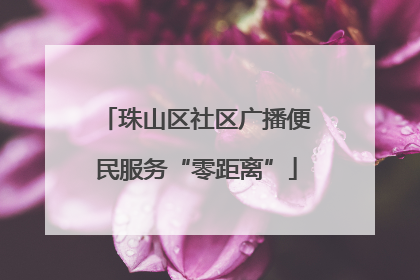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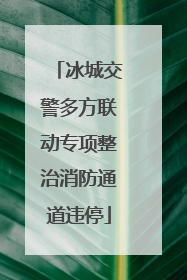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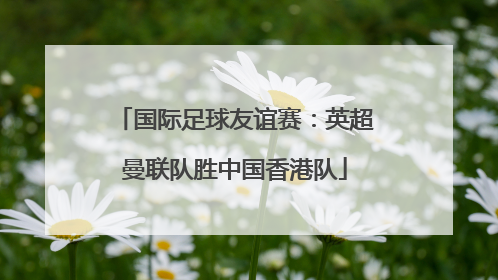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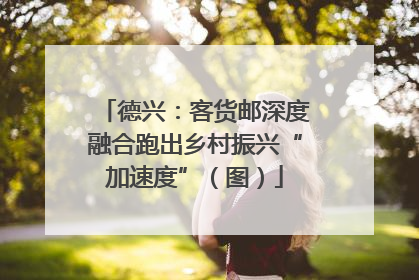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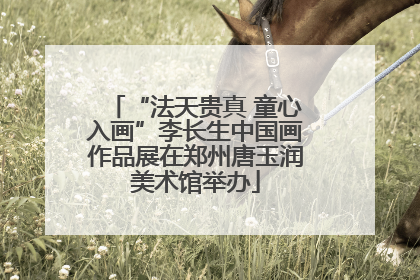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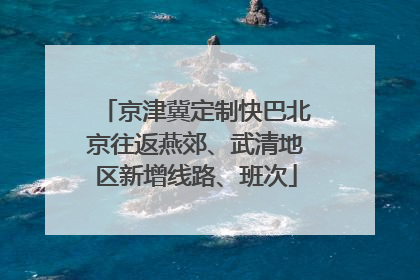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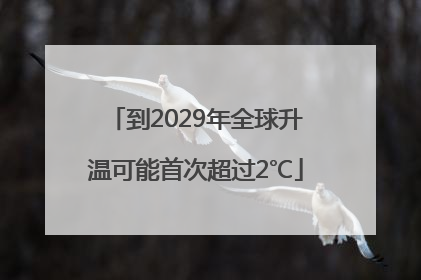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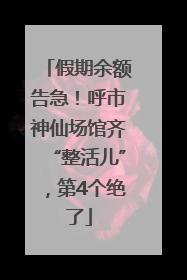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